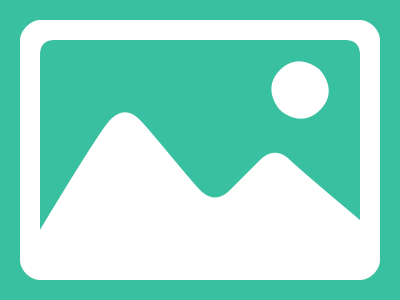我叫小玲,现年25岁,来自一个普通家庭。平时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,负责写一些关于人际关系、情感的专栏。这使我对两性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,也让我对爱情充满了期待。
一天,我遇到了一位名叫李叔叔的绅士,他是一位60岁的香港男人。李叔叔文雅风趣,谈吐中透露着丰富的阅历和人生智慧。我们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彼此的生活,并建立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联系。
那晚,我与李叔叔决定共进晚餐,因为我们之间的默契与互动让我对这个渐入佳境的
常常哭着哭着就笑了,从演员们的演出中,她看到了自己经历里未曾察觉的一面。
去年下半年,95后女生Kiki接连遭遇生活的风暴。硕士毕业后,她迟迟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,不久后,母亲患了重病。白天,Kiki在医院陪伴妈妈,晚上抽了空去做兼职赚钱,整个人像是被“套住了”,没有一点喘息的空间。
直到她踏入剧场,Kiki获得了一种情绪上的松绑。温暖的灯光下,几位演员并排坐着,温柔地凝视着她,全然专注地听着她的故事,她获得了一种无条件的信任。
▲
演员在舞台上温柔注视观众
每场演出的观众通常在20人左右,环境私密、安全
讲述的时候,她常常因为焦虑词不达意,但是演员、乐手总能敏感地领会她的脆弱。她的经历被几个演员即兴地用诙谐可爱的方式演绎了出来,幽默中透露出对她的体恤,“那种感觉像小时候不小心摔倒了,趴在一堆哥哥姐姐的怀里,被温柔地哄着。长大后,这种感觉太少有了。”
剧团的演出流程并不复杂,简单来说就是“你说,我演”。观众先分享一个自己真实的经历,领航员(主持人)随后对观众进行一个简短的访问,最后,演员、乐师会把听到的故事即兴转化为一段戏剧表演。
▲
领航员不仅是主持人,也像是一位“短篇小说编辑”,
负责给每个故事命名、选择故事的演绎形式
▲
乐师需要通过音乐引领故事的发展
这种即兴戏剧的形式名为“一人一故事剧场”(Playback Theatre),起源于70年代的美国。市面上主流的即兴剧都是即兴喜剧,以逗乐为主,但“一人一故事”更加看重对故事深度、心理层面的挖掘。
3年前,85后女孩Rachel第一次接触还原剧团。当时,她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,情感遇到了很大的变故。但作为一个“成熟”的职场人,她必须保持情绪稳定,展现出一副“无坚不摧”的样子。
▲
演员Rachel,3年前她还是还原剧团台下的一名观众
但那天在剧场,她一口气讲出了自己的故事,她感受到了一种“被允许”,无助、悲伤、愤怒,积压的情绪一下有了出口。
她永远记得那个故事的结尾——演员把散落在地上的布一片片地捡起来,抱在怀里,她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力量:“像是自己被压成了很多碎片,然后被人拼起来一样。”
在此之后,Rachel几乎每周都会去看剧团的演出、排练,剧场给了她“真实面对自己情绪”的机会。一年后,她成了剧团的演员之一。
从2017年起至今,还原剧团做过70多场公开演出,演绎的真人故事有1000多个。每场演出都有一个主题,从MBTI、狗屁工作,到性骚扰、我的反派人生,观众的经历分享围绕这些主题展开,个体的故事总能切中当下的社会情绪。
▲
和职场主题相关的演出“谁的工作没烦恼”
今年上半年的一场演出“谁的工作没烦恼”,来源于年初人类学家大卫·格雷伯的著作《毫无意义的工作》引发的热议。
汤包不希望观众止于对职场的吐槽,于是设计了一个开场仪式,大家不能透露自己的职业,而是得用一个动词来描述自己工作的核心,就像你画我猜。
那天,有老师用“陪伴”而非“教书”去形容自己的工作;保险从业者用到了“守护”,意外发生时,保险可以为一个人的生活兜底。演出结束后,每个人再叩问自己:我的工作真的那么“狗屁”吗?
▲
性骚扰主题与巴西柔术结合的演出“抵抗之力”,
铁头现场给观众教授“受身、破把“的技术
今年6月,性骚扰的主题被搬上舞台。演出过程里,有一个女孩袒露,她曾经被迎面骑电动车的男士当场袭胸,但因为恐惧,她没有反击,事后,她只能踢垃圾桶、踢街边的自行车,去表达自己的愤怒。演员铁头觉得这些经历不应该被隐身,只有通过一次次地重申,才能打破长期以来性骚扰背后的集体沉默。
为了不让演出沦为纯粹的伤痛回忆,铁头把演出与巴西柔术结合起来,表演结束后,她给现场的女生指导柔术里“受身、破把”的技术。
▲
演员在演出现场
汤包至今还记得2020年那场抑郁症主题的演出,名为“孤独有多少种样子”。剧团实验性地采用了“声音剧场”的形式,整场演出只有声音,没有画面。观众落座后被轻柔地蒙上了眼睛,黑暗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安全的感受,讲述者的顾忌消失了,变得放松、坦诚,听故事的人也更加专注,汤包说:“一种感官被剥夺,更多的感受被打开。”
有人将一人一故事剧场比喻为安放心事的“树洞”,而且每个心事都是有回应的。
▲
观众常常在演出现场落泪
剧团甚至曾经推出过一个名为“省着点哭”的纸巾周边
也因此,剧场里,眼泪总是猝不及防。有观众讲到自己尘封多年的伤痛,心事突然被轻轻地敲开,声音哽咽;有人讲的明明是快乐的故事,却因为看到生命中美好的记忆被演员们重现在眼前,一下子泪目。
通过演员和乐手的再创作,观众也获得了一个看待自己生命体验的新视角。
▲
主题演出之“内心的结构”
“真的没有托吗?你们是不是商量过了?”在还原剧团的演出现场,时不时会有观众发出这样的疑问。
因为没有剧本、没有彩排,观众面对舞台上“天衣无缝”的表演,时常会发出感叹,演出就像变魔术一样神奇。
默契来源于团员之间的相互信任,成为朋友是“一起工作”的重要前提。
2017年,汤包、铁头和另外两位好友在上海共同创立还原剧团,专注做“一人一故事剧场”。
▲
左:铁头是一位巴西柔术教练:
右:Rachel在一家科技公司做用户研究员
▲
剧团没有固定的演出场地,从书店、美术馆,
到婚礼、屋顶,就像大篷车一样,四处游牧
汤包和铁头都是90后,大黄是80后。三个人中,没有一位是表演系出身的,汤包是学新闻的,铁头曾经做过幼儿园老师,大黄则是一名程序员。剧团没有固定的演出场地,从书店、美术馆,到婚礼、屋顶、草地,四处游牧。
如今,剧团有12位活跃的成员,大家的职业分布在各个领域,从互联网到房地产行业,也有当老师的、做心理咨询师的……这种剧团生活,变成了他们的第三种人生,调剂了大家高度内卷的城市生活。
用铁头的话来说,团队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分是开放的,就像插口一样,需要的时候,大家就能彼此联通。
▲
铁头的家是团队的根据地,
大家平时会在一起排练、做游戏、吃东西
即兴剧的每一场表演都高度依赖演员之间的集体合作。上台前,没有一个演员知道,这个故事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走向发展,甚至连自己的角色都无法预估。当第一个人建立场景,接下来的所有剧情、角色都是在即兴的配合中逐渐形成的。
但即便演员之间知根知底、默契度很高,每次演出仍旧是一场冒险。汤包说:“因为一切无从预设,所以演出前,我们只能把自己的脑袋、耳朵还有身体热开。”即兴喜剧演员出身的金靖曾把即兴比作“跳伞”,“那个极致的快感跟极限运动一样”。
▲
演出的元素多种多样,可能是木偶剧、肢体剧、音乐剧
大家有时候也会遇到那种“演完了才知道对方在演什么的情况”,比如一个跟包子有关的故事,直到演出结束的复盘会,演员才有机会自白:“我刚演的是包子散发出的热气。”
汤包把每一场演出比作演员与观众之间的“猜心游戏”,观众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分享自己的生命体验,演员也要付出真心,最大限度地去摸到一个故事的内里。
表演最大的难度在于“编创”,演员们要根据讲述者自身的特点去进行二次创作。但每一个编创的决定都有可能会惹怒观众,让对方觉得,这不是我想要的故事。
共情观众的感受,是演员们听故事时的基本要求。演员得关注到讲述者每一个细微的情绪变化,他/她在哪个地方停顿了,害羞了,自责了?他/她的腿有没有在抖,有没有抱着手臂……这些细节,都需要演员敏锐地捕捉。
▲
面对观众的讲述,领航员、演员需要全然地倾听
另一个聆听原则是放下评判。有时候,演出会遇到有一定道德争议的故事,但演员们要做的,不是立刻质疑,而是去转换视角,进入讲述者的世界。
很多故事看上去很相似,失恋的心碎、工作的消磨,但其实都带着独一无二的个人印记。例如,讲述者可能会用一个很妙的比喻,或者用很怪的动词。
▲
即兴戏剧中,演出的“意外”也可能是迷人之处,
演员偶尔会在台上直接切换角色,或者用扫场的方式进入下一幕
在“谁的工作没烦恼”的演出里,有观众形容自己上班是一种“沉浸式表演”,汤包立刻感受到了背后不一样的意味——“沉浸式表演,有一种把自己都骗进去的感觉,谁是观众谁是演员,谁是真谁是假,都可以被玩弄。”这种表达,就是解锁一个故事的钥匙。
当然,演出不可能百分百完美,“意外”也可能成为迷人之处。“重点就在于那口气不能断掉,只要我们处理得够丝滑,观众的观赏就不会有那种断裂感”,哪怕演员在某个瞬间陷入了沉默,也没关系,“甚至它会比连绵不断的、特别紧凑的对话,要更加引人深思。”
▲
每个人都能在他人的故事中,看到自己的影子
“这里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,演绎的也是真实的故事,所有的情绪是真实的。”不论是观众还是演员,几乎每个人都会强调“一人一故事”剧场真实的力量。
今年6月,还原剧团发起了性骚扰主题的演出“抵抗之力”,到场的观众里有超过1/3的都是男性,有一名男生感慨:“如果不是这些故事被演出来,我从来不觉得性骚扰和自己是有关的。”
铁头观察到,在场的男性观众仿佛是“被摁住了头”,听这些讲述还不够,还要去观看一遍,这个过程让他们无法把自己从一个个的悲剧事件里“解离”出来,他们不得不去思考,被侵害的人该怎么办?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?
▲
“抵抗之力”的演出现场
不少男性观众表示,更加理解女性处境了
大城市里,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明晰,生活状态原子化,很少有人会愿意走进他人的世界,看到别人的挣扎、脆弱和悲伤。人们更习惯躲在互联网上,用自己的价值量尺去审度别人的人生。在一人一故事剧场这样的安全氛围里,人们获得了一个“看见彼此”的可能。
观众Kiki形容,剧场就像一个“圆圈”,把不同人的经历头尾相接地连在一起,“他/她正在经历的困难是我曾经遇到过的,我现在的经历也许是其他人有过的。大家的故事会巧妙地接合”。
▲
一条的拍摄已提前与现场观众协商并得到允许,相关隐私作模糊处理
为了保护讲述者的隐私,每一场演出不允许被录像、拍摄。汤包形容,这些故事就像沙画一样,演出之后,它们就不存在了。而剧团和观众的相遇,也都是一期一会的。
改变也在演员之间发生。铁头说,因为“一人一故事”,自己变得更喜欢人类了。以前,很多人都让她无法理解,但如今,她更能共情到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。
汤包认为,理解别人的故事,也是在理解自己。从小到大,他都在一个很精英的环境中成长,同学们有很强的竞争意识、狼性精神,高中时,学校辩论队的BBS论坛甚至名为“Elite”(精英)。在这个环境里,他的优等生情结也一度困扰着他。
▲
汤包说,演绎上千个故事之后,他也更能理解自己了
疫情期间,汤包曾在剧场听到了一个高中同学的故事,对方是他觉得“一辈子都无法赶超的人”,一个在东京工作的金融精英。但即使如此优秀,这个同学仍旧非常焦虑,每天他会戴着口罩在东京市区疯狂骑车,一天骑几十公里。
那一瞬间,汤包意识到,精英的生活固然精彩,但和普通人一样,他们也有疲惫、恐惧、焦虑的一面。他开始学着接受“普通人”这个概念里的美妙。
很多人在看完演出以后,常常用到“疗愈”这个词。但汤包觉得“支持”这个词更加准确,如果一个人正在经历情绪难关,那么积极的倾听与倾诉,也许可以将这个人轻轻地托起来,让他/她的情绪疏通出来。
在近期的一场名为“梦境中的我”的演出里,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在问诊过程中被医生性骚扰的经历,梦里,她曾反复回到那个时刻,想要反抗什么、说点什么。演出中,演员们利用舞台上的时空转换,帮她说出了她当时没有说出的话,做出了没有做的事。
“很多时候你不讲出来,你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。说出来,就是变好的开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