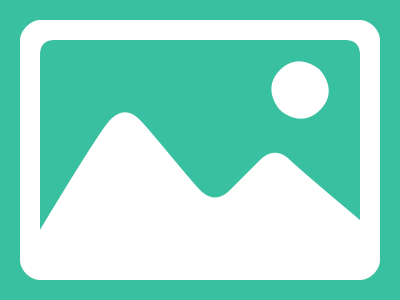文丨花欲燃吖
“斜倚门儿立,人来倒目随。托腮并咬指,无故整衣裳。坐立随摇腿,无人曲唱低。开窗推户牖,停针不语时。未言先欲笑,必定与人私。”
这是作者描写来旺妻形态的一段话,这书中唯有二人最合意,一个是原主宋惠莲,另外一个就是西门庆私仆妻的主要参与者潘金莲。这双莲都是倚门卖俏,搔首弄姿的轻浮人,西门庆对这二人根本无需动什么花言巧语,费什么万般心思,只需要营造一个机会,花上些小钱便可。
可以说能用钱得到的人,
梅并不是提倡性文化的书,相反,它提出了深层的思考:
人类生活中,性该如何定位?
不得不说,性是生命的张力,是社会活力的基础。
我们每日所经历的种种社会活动,都与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撇开性谈世情,等于是无缘之木,抛开性探讨社会与生活,在文学的层面而言,是文学表达的自欺欺人。
健康地阅读金瓶梅,便要对文学表达中的性,有新的、更理性的认知。
概括地说有3点:
首先,“性”的背后是世情。
性虽是在动物性与生物性的驱使下发生,但却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。
文学批评家有一个有趣的概念:“性的政治”。表面上看,金瓶梅的性描写是两个人的事儿,实际上,却是整个社会性别关系的缩影,而性别关系,又是社会关系的基石。
比如,在《金瓶梅》中,西门庆在他所有性行为中,都对女性有居高临下甚至虐戏的态度,这便包含了其作为社会人,尤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官员的男性,占有并支配女性的权利意识。
再比如,西门庆与潘金莲、王六儿等出身低贱女人的性关系既是男女之“性”的,更是家庭主奴之间的,也是一种权力的投影。
更广的维度而言,这便是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所塑造的意识形态。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,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,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
其次,“性”的根部是人性
“性”,是人性格特质最极端表现。
这当然是人最本能的活动,却也是最能揭示人性格中最本质东西的途径。
《诗经·墙有茨》中写道:“中冓之言,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,言之丑也。”
“中冓”便是指性活动,而“言之丑也”,并不是在说难堪,而是在说幽暗隐秘。
从这句诗,我们可以知道,早在千年之前,古人便已经认识到,之行是日常生活中难以言说的,也因此,性描写在文学中担负了反映人生私秘世界的功用,如同裸体画是世俗之“丑”又是艺术之美。
从性入手,探索人性,金瓶梅并不是孤例。
在西方文学家的评析中,英国作家劳伦斯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一书,之所以列于世界名著,便是它那饱受争议的“性”描写,揭示出了人性隐秘的本质。
第三,“性”的深层是链接
性活动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,它是个体与社会的线索、是主观与客观的链接。
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:
“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的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时候开始的,即是从通奸开始的。”
这并不是哗众取宠的歪论,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性伦理对社会的重新建构。
Love这个概念,最初并非指男女之情,而是指基督教的信徒对主的宗教之爱,恰恰是随着西方世界对性行为肯定,男女爱情的Love才走入主流价值体系。
比如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,安娜是一位出轨的有妇之夫,但包括作者和读者,都是站在安娜的立场,对安娜投以悲悯和同情,而鲜有“不道德”的批评指摘。
这在中世纪之前是绝无可能的,正如金瓶梅在成书的明朝,遭到官方史无前例地批评封禁。
说白了,两性关系,是嫁接个体与社会的纽带,不同的两性关系,折射不同的社会形态。
金瓶梅的性描写,是无遗漏地对社会人生上上下下、方方面面描写的真切反映,也因而成了一部中国十六世纪两性生活与儒教“婚姻的镜子。”
即便当不上伟大,也当得起杰出的评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