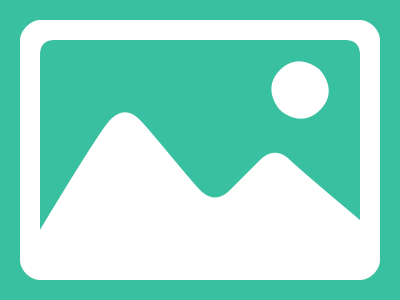隐语,不是常态语言,而是变态语言。原型的直语,直指直称,言即及义,力求明明白白。改型的隐语,不直指直称,曲折迂回,追求不明不白。闻一多先生对隐语界说准确:“它的手段和喻一样,而目的完全相反。喻训晓,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。隐训藏,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”*。直语A就是A,直指那事物,与义是直接的。隐语,与义拉开了距离,A是x。直语,可以直接地接受。隐语,须思辩要经过
就产生不了交感效应,达不到交流的目的。
[一]
《金瓶梅词话》既承袭了前此各种隐语造语方式,又有他书所无独创之隐语。创设隐语,虽然是“揣着明白说糊涂”,但绝对不是杂乱无序的,而是按着一定的法则构造隐语。欲破解隐语,首先应理清“编码”规则。故而本文分疏《金瓶梅词话》隐语种种语构体式,同时揭明书中隐语之谜。
一,离合,即拆字格。此体由来已久。《续汉书·五行志》载有歌谣:“千里草,何青青;十日卜,不得生”隐斥董卓速死。东汉孝女曹娥,度尚为作诔辞,立石。蔡邕夜摸其文读之,题“绝妙好辞”之隐语。人们常举作拆字格之代表。《世说新语·颖悟》又衍为曹操与杨修测智故事:“魏武尝过曹娥碑下,杨修从。碑背题:黄绢、幼妇、外孙、齑臼八字。魏武问修解否?修曰:黄绢,色丝也,于字为绝。幼妇,少女也,于字为妙。外孙,女子也,于字为好。齑臼,受辛也,于字为辞。绝妙好辞也。”后世离合体诗联滥觞,如“古木枯,此木成柴;女子好,少女为妙。”从文字学角度审视,好字金文造象是母子合体,母爱施于子为好;或是先民对生育的称扬。联中好妙二字承袭与增大了“绝妙好辞”旧文人的庸俗趣味。可见“绝妙好辞”对后世影响颇大,且也渗透沉淀到《金瓶梅词话》之中。《词话》以“色丝子女”隐指“绝好”频出。有些拆字格隐语,因习用隐秘性已经泯没,甚至已经溶入普通直语之中。如《词话》中的“女又十撇儿:奴才”,“贝戒儿:贼”等等。
“这刷子踅得紧”,刷子难解。如果拆刷字为“吊刀”,则是隐指男阳,吊、刀同义对举。《西厢记》“你是个木寸马户尸巾”合则为“村驴吊”可证“尸巾”离合非独《词话》。《词话》80回“娘捎出四马儿来了”,四马是别写的骂字。骂,是个形声字。义符两个口字,其声嚣骚。穿凿地谓“声中有义”,马为母,可是“交口”骂娘了。
二,歇后。《金瓶梅词话》中,歇后语颇多。有的因习见而熟知,如“秋胡戏”(妻)、“驴马畜”(生),因习见甚而忘却其为歇后。76回“号咷痛,挖墙拱”是两个歇后的重迭。“号咷痛”明歇“哭”字“挖墙拱”歇“窟”谐哭,属于暗歇。与《红楼梦》“千红一窟”取法相同。一明一暗,两歇迭合,有着层进迭加的力与趣。《词话》45回“秀才取漆——无真”,是谐音歇后。对文人的秀才语含讥贬:谓书呆子取漆不辩真伪,隐所娶之妻丧失了处女的贞元。到了文人修订的崇祯本里变成了“秀才无假漆无真”了。不仅变对文人的贬抑为崇扬,而且破坏了歇后语:不歇后了。丧失了语趣。明·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卷34》“谚云:黄岑无假,阿魏无真,以其多伪也。”到了《增广贤文》里变成了“黄金无假,阿魏无真”,阿魏因中国不产,主产于伊朗等地,故伪者多,那么“秀才”何以无假呢?文人极力改铸俗谚,使之符合自身及本阶层的利益。
三,藏头。“望江南、巴山虎儿、汗东山、斜纹布”,这个隐语兼格谐音、卷帘,然而主格却是藏头。望江南是词牌名,巴山虎儿是植物名。汗东山人谓曲牌名,或是卷帘即山东汉,有鲁地色彩。如李渔批语所云“方言隐语,含讥带讽”。斜纹布是纺织品名。省略为隐蔽“头”而故设的迷障,所藏之“头”便显露了出来,是为“望巴汗斜”。再循所谐之音即为“王八汗邪”;望巴,即王八;汗邪即汗憋的。
王八为龟之俗称。龟在唐时尚被视为吉祥之物,龙凤麟龟合称四灵。时人常以龟命名,如李龟年、陆龟蒙等。殆到元代始讳龟,并以之辱妓或妻有外遇之夫。何故呢?清翟灏《通俗篇》“又以妻之外淫者,目其夫为龟。盖龟不能性交,纵牝者与蛇交也。……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,盖古赭衣。”清代小说《九尾龟》“那教坊中的人役,皆头裹绿巾,取其象形,不似乌龟?列公试想,那乌龟一头两眼,不多是碧绿的么?还有取义一说,是龟不能交,那雌龟善与蛇交,雄不能禁;因此大凡妇女不端,其夫便有乌龟之号。”古人不见龟交而把啮蛇龟啮蛇误认为与蛇交。遂以此指妻有外遇者,至于“礼义”的忘八无耻,则是文人的附会。
四,反切。拆字是字形的离合,反切则是字音的离合。字音的切分与拼合,古人谓之“急言”、“缓言”。宋·沈括:“二声合为一字者:不可为叵,何不为盍,如是为尔,而已为耳。”南宋郑樵:“慢声为二,急声为一:者焉为旃,者与为诸,蒺藜为茨,不律为笔。”《词话》中骂应伯爵是“丑古来子”、“极古来子”,迄未有解。急声合“古来”为一字,是为“怪”字,子为贬蔑之后缀。语得解,即“丑怪子”、“极怪子”,为贬骂之词。
五,谐音。“穿黑衣,抱黑柱”,注家因不明其所谐为鲁方音,望文生义解作:“穿黑色的衣服,抱黑色的柱子”,鲁方音今犹有读“谁”若“黑”者,明乎此此语得解:“穿谁衣,保谁主”,“抱柱”谐音“保主”。
“鬼酉儿上车——推丑!”歇后与制谜皆忌底面犯复,因不能露白出“丑”,故将繁体“丑”字拆为“鬼酉儿”(又是拆字格)。关键“推”字所谐的是鲁方音,鲁地读太、特若“推”。义即杨雄《方言》之“无偶曰特”。推,又是双关,所推之车为鲁地之独轮车。“推丑”即特别丑,丑的无比,丑的出奇,丑的“没对儿”(无偶)。此语虽兼具歇后、拆字、双关及谐音诸格,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建立在鲁音基础之上,离开了鲁音便失去了此语赖以存活的基础, 证明着《词话》与鲁方音有着不解之缘。如果不是从语音, 而仅从字词上难于判定其为鲁方言,而隐语中的鲁方音为鲁地所独有, 可为硬证。证明着《词话》不是文人之作,而是熟悉鲁方音的说话人的实录。(另撰《鲁音征实》详论)。
六,连环。其他隐语结构虽然与直语不同,已经由如桥的静态线性结构,变为如船的动态非线性结构。然而,其他隐语大多是“谜面”直扣“谜底”;语构虽有所改变,然级数不多。而链式结构在编码时,多级加秘。且以“半边俏”为例,语构链犹如九连环,一环不开全语难解。注家因不明其造语链,误释为“半边瘫”、“半瓶醋”。“半边俏”之语链,相当于“承启式”。如下列公式:因为a=b、b=c、c=d,所以a=d。“半边俏”为男阳之隐语,分解如下:
1半边俏, 整体的哪半边?“左边的”!《水浒》《词话》皆以“左边的”作为骂语。
2“左边的” 何指?道教四帝之一的真武大帝之原型为龟蛇同体。人化了的神象,于神象两侧分置龟蛇二将军。龟将军居左,“左边的”隐指龟。
3以龟隐指男阳因其形似。《词话》中有壮阳“养龟”之说。
承启式的语链,如《文心雕龙》所说“辞生互体,有似变爻。”正因变爻之曲折,所以隐语难明。
七,多元,不拘一格。一语一格易解,“硝子石望着男儿丁口心”便因一语多格而难解。
硝子石现代汉语不存,隋唐时有些汉语词为日语所借贷,硝子石日语今犹存。日语玻璃即“硝子”,读音为しょうし。日语不仅汉字渐减,读音也西化改从ガラス了。转而检点中国古典籍,“硝子石”指假玉、人造水晶等(为省,不具引)。《词话》《红楼梦》皆明言“硝子石”是假玉。《词话》李瓶死,应伯爵梦断玉簪:“这折了的是玉的,完全的倒是硝子石。”《红楼梦》写围屏“中间虽说不是玉,却是绝好的硝子石。”可知,它是假玉、假水晶、人造琉璃之类。据书中语境判断,隐指眼睛。俗称病眼为“玻璃花儿”称难看的眼睛为“琉璃泡儿”。
望着南儿取的是谐音格,即望着男儿;丁口心取的是卷帘格,词序倒置,倒转过来是“心口丁”。
全语宜为:琉璃泡儿(的眼睛)望着男儿的心口丁。或喻有眼无珠欤?
[二]
直语,是开放型的,大家明白。隐语,是封闭型的,排他的,只让“约定”的对象明白;隐语只在特定的语圈内流行,不为外人道,当然也就不是圈外人所能理解的了。
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隐语,便是当时的人甚或书中人物有时也不得其解。应伯爵“吊子曰儿”的隐语,吴月娘便不知所云。应伯爵所说的隐语,属于“妓谈”,清·黄允交《杂纂三续》谓:“坊妓私谈——难理会。” 确如所说,此类隐语殊难索解, 历来被注家视为难点, 现择迄未得解者, 试解如次:
一,零布。
应伯爵骂三个妓女为“三个零布”有如射覆。零布即布头,整匹论尺,布头论块,无须尺量,或为无尺(耻)。又,零布是从整匹上“破”解下来,布又为古之货币,又可能为“破货”。未敢自是,俟方家。
二,“寒鸦儿过了就是青刀马!”
此语学界视为《金瓶梅》隐语之最。欲明此语先须破解另一难解的隐语:
“鸦胡石影子布朵朵云儿了口恶心”此语取的是藏头格,去掉附加的迷障成份,抽绎出所藏之“头”,是为“鸦影朵(躲)了”,明乎此,便掌握了解开“寒鸦儿”隐语的钥匙。两者虽异构然同义。
欲明“寒鸦儿”与“鸦影”,须与唐诗相较。王昌龄《长信宫秋词》有句云:“玉颜不及寒鸦色,犹带昭阳日影来”。比较是以诗解语,并不是征实语源于诗。诗与语共同点在于寒鸦儿掠去日影,大有《西厢记》“槐影风摇暮鸦”之意。“鸦影躲了”,日之夕矣,夜之至矣。应伯爵发语重心在于时候不早,“我等不的了!”
青刀马当然不是直指语义,而是几经曲折:
1,刀马指脚, 宋·汪云程《蹴踘谱·圆社锦语》“刀马,脚”。邓王宾《村里迓鼓·仕女圆社》套“俊庞儿压尽满园春,刀麻儿踢倒寰中俏”。
2,脚,隐指男阳《词话》常以人体某一局部代指另一器官。如“管人吊脚儿事”,因脚有根柢义,“底脚里人”即知根柢的人。吊脚同义对举,义为“吊”事,或有双关之义?
3,青,《江湖行话谱》“大刀为诲青子”。《切口大辞典》“青子亦为刀”。明·朱有燉《诚斋乐府·乔断魂》“青资,是刀儿”。刀,本是男阳之隐语,今时川皖等地仍有言童阳为“小刀刀”者。
总上,全语谓: 寒鸦过(或鸦影躲),天晚了,耍大刀了。
三,有关两性关系及器官的隐语,书中颇多,甚至武大的诨号“三寸丁”也是隐指男阳。诨名虽然承袭《水浒》,然《词话》扩大了调谑之深意,“俗语言其”如何,明指其为当时俗语。书中人物常以“三寸货”作骂,如“贼三寸货”(31)*、“火燎腿的三寸货”(20)、“没挽和的三寸货”(51)等等皆可为证。《新刻批评金瓶梅》(通称崇祯本),在二回“自家骨肉”句上,有戏笔眉批:“语云:三寸入肉,强如骨肉。”“语云”便是当时俗语常云之意。元杂剧《百花亭》“单则三寸东西不易降,专在百花丛中作战场”,也可证明其为元明时之常言。延至清,语犹存;小说《肉蒲团》也以“三寸东西”隐指。实则“三寸货”即“鸟货”非他。吉版《词典》谓“言其矮小”,魏子云先生谓“指长不大的人”皆误。误解盖因书皆言武大“生得短矮”:《水浒》“身不满五尺”,到了《词话》成了“身不满三尺”。明尺为31.10厘米,五尺为1.55米。《词话》中潘金莲寻思:“身不满尺的丁树”。不满三尺已属夸张之言,“身不满尺”,疑有夺字,不然便夸而失真了。“丁树”之诨名隐拟以男阳;不仅喻其外貌之“猥衰”,且也喻其内质之“懦弱”。(“没挽和的三寸货”,解为今语: 没救的熊鸟货,可为“丁树”之参注)总之,诨号之创名取义,提挈着“这一个”人物的全般。
“甚么话?檀木靶!没了刀儿,只有刀鞘儿了!”(35),因系隐语,迄无确解。偶见《太平广记》引《启颜录·崔行功》“唐崔行功与敬播相逐,播带榈木霸刀子;行功问曰:‘此是何木!·播对曰:‘是拼榈木!’行功曰:‘唯问刀子,不问佩人’。” 应伯爵与崔行功皆是以隐语俏骂对方,把对方等同于刀与靶。刀隐男阳,《易·归妹》“离为刀”。今皖西仍戏呼婴幼阳为小刀刀。栟榈木又名花梨木似紫檀,(见《本草纲目·木部二》)故与檀木同。靶与刀同体,可代指同一事物。“甚么话?檀木靶!”以木之色质设喻,可以解为“甚么话?那话儿!”“没有刀儿,只有刀鞘儿了!”贬蔑对手无阳刚之言以对,只剩下一张×嘴了!
一九八八年芜湖红学会上与蒋和森先生邻室而居,蒋先生询及《金瓶梅》及其他小说, 何以“蹄子”作骂?初以为是把人兽化,然终觉未安。小说中“蹄子”不是指一般的“畜生”,而是特指淫妇。《儿女英雄传》“谁知越劝倒把他劝翻了,张口娼妓、闭口蹄子。” 语中娼妓与蹄子显然是同义对举的。
宋·庄绰《鸡肋篇》卷上“南方举子至都,讳蹄子。谓其为爪,与獠同音也。”此说虽未中的, 然提出因蹄为爪而讳。兽为蹄,禽为爪,人为脚。脚,俗称鸭子(丫子)。“蹄子”并非以爪同音之獠(男阳)作骂, 倒是以脚之同义俗称“鸭子”作骂。宋时浙人讳鸭,因其乱淫。《鸡肋篇》“浙人以鸭为大讳,北人但知鸭作羹虽甚熟亦无气, 后至南方乃知: 鸭若只一雄虽合而无卵,须二三始有子,其以为讳,盖为是耳,不在气也”。郓哥骂武大“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,在锅里也没气!”符合着庄绰所说北俗。武大回答却又暗合浙俗:“我老婆又不偷汉子,我如何是鸭?”指明偷汉者及其夫皆为鸭。准此, 蹄→脚→鸭=淫妇。语得解。和森先生以为然否?
涉及两性关系的“扒灰”、“回炉复帐”“九燉十八火”等等,均不是今时注家所释,皆从道家采补衍为俗语,不一一论列。
性及其器官为什么讳言呢?因其“本体不雅”**,不能直指,不能直称。《词话》称器官为不便处,不是望文生义的“不能排便”;而是不便于称说的“难言之隐”。人的“本体”,由生殖崇拜之圣洁,何以跌落到需遮隐的“不雅”? 学界歧说:或谓遮诱、或谓遮羞。其实诱与羞之遮,那是较晚的事;原初只为遮护: 保护脆弱而神圣的繁衍人类的部位而已。进入了文明人时代,才有了“本体不雅”的观念,遮羞与遮诱才与之伴生。因其不雅,在语言中才须遮饰。这是受制约于社会道德的规范。“本体不雅”,变体使之雅驯,为体面意识所容许。不伤风化,而诉诸大雅了。
隐语的产生,导因于“难言”: “难言之隐”是隐语生成的基因。还须指出:本体雅者,并不难言的隐语也颇为不少。不雅者是不便明说,雅者是不愿明说。刘勰“遁辞以隐意,谲譬以指事”。“遁辞”的隐语,隐去粗鄙的本体,雅化为了习俗能够接受;而谲譬并不粗鄙的本体追求的是人们乐于接受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语言趣味,语趣追求的是审美效应。人们充分利用汉字形、音、义的特点创设隐语。一为隐蔽直言、回避禁忌;二为强化语言趣味,增强语言艺术的审美效应。有些隐语由于长期使用已经不隐不趣,因其淹没在“普通话”之中,故而人们再造新的隐语求隐求趣。“王八”已失去刺激的棱角,遂产生新的变体:如“望江南、巴山虎”,又如书中骂李铭、李惠以及韩二是“二打六”,二再搭上六,是为八,即王八的新的变体。书中妓院称龟奴为“八老”亦取此义。前面说到习俗是隐语的制约力,“秽污词,市井气,切戒之”已经作为“圣人训”写进了蒙经《弟子规》之中,然而《词话》中秽言亵语不胜枚举。追求的是俗人的俗趣,而不是文人的“雅”趣。可见《词话》的写录者,是“市井气”的说话人,而不是凛遵“圣人训”的文人名士。
[三]
离合体为隐语结构主要形式之一,故本文列在篇首。然而注家常将“拆白道字”与“拆牌道字”混为一谈。两者并非一事,不容不辨。
拆白道字,“白”作破白解,元杂剧“慢慢白他谎”,即取破白义。拆白道字,亦即拆字格。《西厢记》“我拆白道字,辨你个清浑。”“拆白道字”明确地指后文“你是个木寸马户尸巾”的拆字格。《水浒传》61回“拆白道字、顶真续麻,无有不能、无有不会。”“拆白道字”与“顶真续麻”对举,也足能证明两者同属文字游戏。
“拆牌道字”不是拆字之戏。也举几例以为证。《西游记》12回“行令猜拳频递盏,拆牌道字漫传神。”元·戴善甫《玩江亭》“打双陆、下象棋、拆牌道字、顶真续麻,无所不通、无般不晓”。《金瓶梅词话》80回谓潘金莲“拆牌道字、双陆象棋,无不通晓。”《西游》把“拆牌”与“酒令”并称;《词话》把“拆牌”与棋戏对举。可见,它是“牌”戏,而不是文字游戏。所拆的是牌,所道的是由牌而化出的令。《词话》21回掷骰行令的描写,可以作为“拆牌道字”之实证。四只骰子组合为两张牌:拆而为骰、合而为牌。同时也表明骰与牌的亲缘关系:牌是由骰子衍生的。
骰子,为正六面体。每面一个点数:由幺至六。骰子的点位是固定的,六面为三组对称面,每组相加为七。元杂剧《度柳琴》称之为“色数儿”即幺六、二五、三四相对。每张牌的牌式是由两只骰子组合而成的。两只骰子可以组合成21种不同的牌式。公式为
公式前半部为他配对,还须自配对所以要加n。得天地人和,三长,四短,十一种;每种一式两扇为二十二扇。杂牌五种十式十扇。总计如书所言“牙牌三十二扇。”*
《词话》21回令规是“照依牌谱上饮酒,一个牌儿名,两个骨牌,合《西厢》一句。”所依之牌谱,与今传世宋·朱河《除红谱》明·瞿佑《宣和牌谱》以及明·王圻、王思义《除红图》皆明显不同。所以,所依何谱待问。所谓“拆牌道字”,便是依谱“拆牌”道《西厢》与牌关合之文字。因为“拆牌道字”也是隐语,而且是特殊的隐语,不应无说。现参详各谱,分解如下:
一,吴月娘“掷了六娘子,醉杨妃,落了个八珠环,游丝儿抓住荼蘼架。”
这是两张“和”牌,即“对儿和”。
诸谱皆以“幺”为珠。“和”牌为骰子的“幺”与“三”点构成。两张“和”共为八点,是为“八珠环”。“斜三儿”又象征“游丝儿抓住荼蘼架”。按,令规“合为《西厢》一句”,《西厢》句为“玉簪儿抓住荼蘼架”,又有句:“游丝儿牵惹桃花片”。因酒令关合着人物性格与命运,“和”牌,喻月娘性平和。归宿如“游丝儿”。不用“牵惹”恐唐突其人。将两句揉为“游丝儿抓住荼蘼架”。
二,西门庆“我虞美人,见楚汉争锋,伤了正马军,只听见金鼓连天震。果然是个‘正马军’吃了一杯。”
两张牌为“虎头”与“花九”。
古战阵盾牌为虎头形。“虎头”牌式为“五”与“六”构成。“六”为“天牌”之半;“梅花五”又象鼓形。故言“金鼓连天震”。
另一张牌为“花九”。“红四”与“梅五”皆为花,与“虞美人”相吻。“楚汉争锋”:汉象赤、楚象黑,与“红四”“黑五”相合。
又,两张牌上同有“黑五”,“黑五”是“正马军”主要部份,故言“伤了正马军”。
“虎头”与“花九”合起来为“辟食”——俗言:“虎头钻酒篓,一个点儿也没有”,两张牌合成为逢十之点数,为必输之绝牌,所以罚酒。元杂剧《谢天香》“幺四五骰着个‘撮十’……二三五又掷着个‘乌十’。”俗言“毙十”,或是“辟食”,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“安谷则昌,绝谷则亡”,绝食是为“辟食”则亡。
三,李娇儿“水仙子,因二士入桃园,惊散了花开蝶满枝,只做了落红满地胭脂冷。”
诸谱蝶为“二点”、花为“红四”。《词话》59回“爱香儿出了个地牌:花开蝶满枝。”蝶即指地牌。“二士”为两个“幺”;“入桃园”为两个“红四”。“惊散了”两幺、两四并不各在一张牌上,而是分在两张,构成一颠一倒的两张“五点”。
幺与四同为红色,故言“落红满地胭脂冷”。《西厢》“落红满地胭脂冷,休孤负良辰媚景”,有讥讽李娇重操妓业之意。
四,潘金莲“鲍老儿,临老入花丛,坏了三纲五常,问他个非奸做贼拿!果然是个三纲五常,吃了一杯酒。”
两张牌一为“长五”、一为“虎头”。
五常易解,名“长五”或“五长”。由两只“梅五”合成。
“虎头”,“梅五”为花,骰六点最多为“老”。“虎头”由“五”与“六”组成,(再加上五常的两个梅花五,是为花丛)故言“临老入花丛”。“虎头”五点为“五常”之半,六点为“天”(夫纲)之半。故言,“破坏了三纲五常”。《西厢记》“谁着你夤夜入人家,非奸做贼拿”讥讽杀夫私婿破坏纲常的乱伦行为。
五,李瓶儿“端正好,搭梯望月,等到春分昼夜停,那时节隔墙儿险化做望夫山。”
两张牌一为“幺六”、一为“人牌”。
俗谚:春分秋分,昼夜平分。天地二牌代指昼夜。“停”,即平分天牌地牌之半,组成新牌,是为“幺六”
“搭梯望月”指“人牌”。59回“那爱月儿出了人牌:搭梯望月。”
然所望之月却是另张牌“幺六”之“幺”。故言“隔墙儿”。《西厢》“为一个不酸不醋风流汉,隔墙儿险化做了望夫山。”隐指李瓶儿“隔墙密约”,气死前夫花子虚与后夫蒋竹山,墙儿岂不成了“望夫山”!
六,孙雪娥“麻郎儿,见群鸦打凤,绊住了折脚雁,好教我两下里做人难!”
两张牌一为“斜七”、一为倒置“二六”。
诸谱皆以红四为凤、斜三为鸦为雁。“鸦打凤”是三、四合成的“斜七”。
“两下里做人难”指“人牌”的红四被分置在两张牌上。倒置的“六套儿”,红四在上、二点在下。在下之“二点”正好成为另张牌三点“雁”之折脚。孙雪娥地位卑微,名为主子实为奴仆。象个“折脚雁”,常常是“两下里做人难!”
七,孟玉楼完令:“念奴娇,醉扶定四红沉,拖着锦裙襕,得多少春风夜月销金帐。”
诸谱“销金帐”皆为“锦屏”与“人牌”。
“四红沉”指红下沉到底,是为“人牌”。“锦屏”象灿烂的锦裙。孟玉楼始为富孀、终为贵妇。三易其夫,“得多少春风夜月销金帐”; 此句是从《西厢》“鸳鸯夜月销金帐,孔雀春风软玉屏”化出。
以上七令中,六娘子、虞美人、水仙子、鲍老儿、端正好、麻郎儿、念奴娇等皆为词曲牌名。与牌式与《西厢》句意,共同关合着西门庆及其一妻五妾的性格与命运。如搭梯宜“端正好”,反讽李瓶儿不端不正。孟玉楼三易其夫则冠以念奴娇等等皆有寓意。词曲牌名在宋明之时,已被用作牙牌之名。以朱河《除红谱》为例,牌名即有蝶恋花、鹊踏枝、雁儿落、快活三等等。由此可见,词曲与骨牌之互渗关系,与酒令共同是俗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份。寓人物命运于牌谱酒令之中,又开了《红楼梦》之先河。
参考文献
闻一多《神话与诗·说鱼》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。
*本文所涉语释均收入专著,书稿已交天津百花社。
**刘勰《文心雕龙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