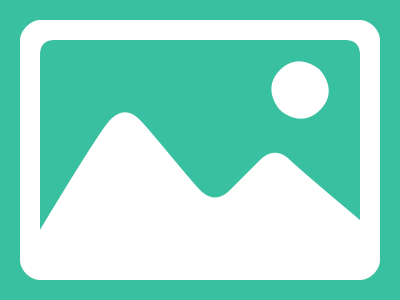业内人士认为,高以翔录综艺猝死只是“偶然事件”,背后更多从业者的“过劳”与事故上不了热搜。
记者/陈龙
“为什么说影视行业都是青春饭?全都在透支生命做节目。”2019年11月27日台湾男艺人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时猝死的消息传出,节目制作人苏蒙克首先想到整个行业的氛围。她说,“这个行业的畸形在于,所有人都把熬夜当敬业。大家被一种虚无的荣耀感笼罩,好像连续多少天没睡觉有多值得骄傲。”
“降薪令”的出台,导致演员片
节目的要求。
尽管微博“高以翔超话”上充满了指责浙江卫视的声音,但影视娱乐的庞大机器依然在运转,行业内部的运行机制还是硬生生地在那里。高以翔之死,在业内人士看来,只是个“偶然事件”。
“崩溃”
11月27日一早,许多不知道“高以翔”这个名字的人都被刷屏了。而知道这个台湾明星的网友,则开始了一场网上的追责和讨伐。
事故发生在凌晨。浙江卫视综艺节目《追我吧》在宁波的片场录制,到凌晨1点45分,奔跑中的高以翔突然倒地。据现场观众描述,高以翔倒地后的片刻,所有人都没在意,还以为是节目效果。屏幕上,摄像师甚至给高以翔的眼睛拍了特写镜头,还是同在现场的明星黄景瑜最先发现“他的眼睛不对劲”。
现场人员对高以翔做了15分钟的心肺复苏,2点之后,他被送往4公里外的医院。微博博主@吃瓜群众CJ 透露,“情况很严重”。大约5点30分,传出高以翔死亡的消息。后来浙江卫视公布的死因是“心源性猝死”。他年仅35岁。另据其好友透露,高以翔此前有感冒症状,原准备29日为朋友婚礼当伴郎。
据粉丝们梳理,高以翔23日去厦门参加完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,25日在台湾,26日凌晨1点多发出最后一条微博,26日下午1点30分抵达宁波,上车前还向粉丝招手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。
27日,大量网友发微博和朋友圈悼念高以翔,并提到他饰演过的角色“王沥川”。而浙江卫视姗姗来迟的“说明”,引发了批评和质疑。网友依据众多来源不一的消息和材料,指责浙江卫视缺乏安全措施、现场救援不及时、节目难度过高、掩盖事故消息等。浙江卫视第二份战战兢兢、语句重复的道歉声明,又被批缺乏诚意。
苏蒙克觉得,一味指责浙江卫视有些不公平。“就像一本书《崩溃》里写到的,大家都处在一个庞大、复杂的行业系统里的时候,每个人都只能注意到很小的范围,而各个环节又环环相扣,联系紧密,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状况。这样就极容易发生崩溃的事情。”
高以翔倒地之前,现场目击者还表示听到他大喊“我不行了,我不行了”。
高以翔的事故,在她看来,也是一场综艺节目,甚至是整个综艺圈和影视行业的“崩溃”。
例如,粉丝注意到,高以翔出事前已经喊着“我不行了”。“正常情况下,很多演员都会说‘我不行了’,‘我累了’”,但包括导演,几乎所有人都没注意到危险,“因为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,每个人都集中在自己做的事儿上。”而导演的背后,有庞大的团队、资金问题,“这是一个如此大的游戏,很多事情就不可控。”
事后,有网友回顾了《追我吧》的内容设计,以及当期录制和往期节目中的危险场面。这档“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”包含“蜂巢虫洞”“平衡滚筒”“爬楼速降”等环节,其中最后一关需要明星吊“威亚”徒手攀爬70米高的大楼,再从楼顶借助滑索,从钢索上滑降140米。此前,吴宣仪、宋祖儿参加该环节时,均曾表露出惊惧的神情。
但苏蒙克说,一般来讲,参加综艺节目的明星事先都与节目组签订了合同,合同中规定的节目内容、时长等都是艺人接受的,艺人及其经纪公司应该对艺人的身体状况和时间有基本的把握。她并不认为,这个极限挑战强度过大,“跟好几年前一些让明星去蹦极、跳伞这样的节目,有什么区别呢!”苏蒙克觉得,此次事故中,经纪公司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。
对于高以翔的死亡,许多明星都出来表达自己参加综艺节目时类似的危险甚至“濒死”体验。28日,男明星姜思达在微博上发文,指高以翔事故背后是“野心、集体梦想、健康、幸福生活指数、金钱、攀比心的混合斗争”。
苏蒙克认同姜思达的说法。她说,如此超时长、高强度的工作,所有人依然拼命参与,“因为我们热爱这项事业。”苏蒙克说,“导演愿意晚上两三点去熬夜开会,大家愿意加班录节目。如果没有热爱,是支撑不下去的。”
而这层热爱背后,是影视行业的大变局。
“限薪令”后,艺人收入缩水九成
已从事综艺、网剧、电视剧制作人工作8年的王凯华说,《追我吧》是当前国内真人秀挑战竞技节目的一个演变个例,融合了此前的《跑男》《全员加速中》等通关闯关类节目,“其实就是大杂烩,全是不同类型的嫁接。”
王凯华觉得,近些年,国内极限挑战类综艺节目越来越多,一端是综艺本身的要求,而另一端是观众需求端的猎奇心理。
“观众就想看更精彩、新奇、刺激的东西,电视台希望更高的收视率。”因此,出现如此高难度、危险性大的节目,客观上也是市场主导的结果。矛盾的是,事前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、贡献了《追我吧》CSM69城市网收视排名第一的好成绩;事故发生后,又集体出来责骂制作方。
“现在的舆论矛盾点都集中在浙江卫视身上。浙江卫视肯定是有问题的,但这是一个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,而不单单是浙江卫视的问题。”王凯华说,浙江卫视的被动地位,造成他们“说什么都是错的”,招来骂声一片,“自媒体时代,每个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更通畅了,但是阴谋论的观点也更盛行。”
高以翔到达片场开始录制的时间未知。腾讯《贵圈》称,“当夜(26日)12点,他被节目组的车接到录制地——宁波环球航运广场”,而当日白天好像已经经过一轮彩排。
据称,浙江卫视的录制从26日早上8点30分开始,至次日1点45分,时长17个小时。事发后两天,网上充斥着高以翔“连续录制17个小时”的说法。实际上,从离开宁波机场的时刻算起,高以翔的工作时间最多12小时。但网上舆论已经无法冷静看到这一误差。
另一方面,从韩国引进这一类节目的过程中,国内缺少了一个把控限度的环节。“韩国的节目导演,在设置一些关卡、障碍的时候,往往要先去挑战体验一下。他们会亲自体验,觉得自己能承受能忍,节目才会去做。”但国内通常不是这样,“你让他自己去闯,他也没有把握完成。别说日常天天休息不好的艺人,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,往上攀登70米,也挺费劲的。”
高以翔灵堂内景。
而“吃瓜”观众最后在屏幕上看到明星们惊险闯关,只是沉浸其中,感受刺激。“看节目和真的去体验挑战,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但在这里,真实体验和“节目效果”的界线变得模糊了。
除了27日的高以翔、黄景瑜、陈伟霆等人,前三期参加节目的还有范丞丞、李振宁、毕雯珺、钟楚曦和前运动员李小鹏、邹市明等。“你看参加这个节目的嘉宾,大多数都是演员。为什么演员现在愿意来参加综艺呢?”
答案是“限薪令”。2018年,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多轮“限薪令”,9月规定,单期综艺单个艺人的片酬不能超过80万,常驻嘉宾一季节目总片酬不能超过1000万;11月进一步规定,影视剧演员片酬,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%,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%。这给一线明星的收入带来巨大打击。
以浙江卫视此前一档经典节目中的女明星A为例。王凯华说,一般综艺每季12-14期,一季打包的费用,A可收入8000万;而限薪令后,她一季的收入只有720万。而从2018年8月开始,受范冰冰事件影响,明星所得税率从原本6.7%飙升到42%,这让明星的收入呈断崖式下跌。
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。”王凯华说,许多明星的消费习惯、心理认知没有适应这个变化。“收入萎缩到1/10,相当于一个普通人,我以前拿一万,现在拿一千。”许多艺人因此不得不接受来钱快,且可以维持出镜率的挑战性综艺节目。
收入下降,给明星带来的心理焦虑也是明显的。一线女演员B,在影视界有着巨大的粉丝量,此前一部剧的片酬在1亿左右。2019年,B所在的公司为她接了一部戏,消息传出,粉丝们以“为什么去给新人小鲜肉抬轿”为由集体反对,B只能拒了这部戏。但她因此得罪了片方,导致2019年无戏可接。“一时半会儿片酬降不下来,没有人去找你。她只能通过综艺节目去维持热度和曝光率,总比没有工作要好啊。”
影视寒冬下,平台却变强势
高以翔死后第二天,有人统计,超过40位明星在微博上发布了悼念高以翔的文字。演员宋佳说,“高危职业,同行们热爱的同时请保护自己”。某种程度上,这也是艺人们一次集体宣泄情绪的呐喊。
明星“身价”和收入下降的背后,是影视寒冬下影视行业资金规模的锐减和利益的再分配,这进而产生了各种连锁反应。
演员身价虚高、“天价片酬”,曾是中国影视界的一个畸形现象。2018年“限薪令”甫一发布,就有人预测,综艺节目可能减产。如今,这已是寒冬里的事实。
王凯华说,目前,中国一线的互联网平台,除了芒果TV之外,全部都在亏损。“节目平台两个最大成本,就是带宽成本和内容成本。带宽成本是国家规定的,没办法;所以只能减少内容成本,而内容成本的很大一块,其实就是演员片酬。”
过去,一些网剧成本逐年攀升,高达3亿到6亿。2017年头部电视剧《如懿传》成本5亿,仅周迅、霍建华两位主演的片酬就占去一半,很多时候,一些主演的片酬甚至占到全部演员片酬的80%-90%。
当年国家政策支持、影视市场繁荣的大环境,直接导致了演员身价虚高。“他们实际上可能并不值这么多钱,只是因为有资本的大量涌入,他们是稀缺资源,有叫价能力。把自己的价钱叫得那么高,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价值就那么高。”王凯华说,“资本撤走之后,价值和价格偏差就不会那么大了。但是演员的心理落差会很大。”
降片酬,曾经也是制作公司和平台一直呼吁的。而如今,当这种呼吁最终实现的时候,行业形势也发生逆转,压力转移到了演员一方。
高以翔遗体返台前夕,粉丝在殡仪馆的花圃旁摆放了超过百束鲜花,并用千盏LED灯结成灯河,每隔一段时间就集
据《证券时报》报道,2019年前三季度,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共646部,比2018年同期的886部减少27%;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共24617集,比2018年同期的35209集减少30%。其中,横店影视城的开机率同比锐减45%。如此行情下,许多一线明星也无戏可拍。
演员迪丽热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说,自己已经七八个月没有拍戏了,她公开喊话导演,说自己“有时间”。同时,《演技派》《演员请就位》等演员养成类综艺节目却热度上升。
在影视剧数量减少、资金外逃的趋势下,头部聚集效应愈加突出。于是,一些收视率高、资金量充足的节目,成为明星们渴望的“蛋糕”。
王凯华透露,影视生产环节中的制作公司、演员、平台三大角色中,平台如今逐渐成为“大托拉斯”。“现在平台强势程度已经到了什么地步?三家联合。第一家说,我们不用这个演员,OK,那两家也说不用这个演员。那这个演员在市场上就没有活路了。”
如此一来,过去身价上亿、动辄耍大牌的明星们,如今反过来要看平台的脸色行事。“最怕的一点,就是得罪平台。”王凯华说,几年前,演员文章在杭州参加一个节目,临上场前提出“要吃油泼面”,否则不上台。这样的情况,今天不会再有了。买方市场已经变成了卖方市场。
因此,和电视台签的合同上关于“工作时长”的协议,就是一纸空文,明星们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合同规定来。“大家的习惯是,这事没做完,无论是谁的问题,咱们先把这事做完,再来理论法律、加班这些东西。”超长时间工作,反倒成了不成文的行规。当高以翔、黄景瑜们录制节目时,他们遵守的,同样是这个行规。
现在,演员在录制过程中不敢再提出格的要求,因为一旦得罪平台,他将遭到遗弃;如果拒绝加班或故意怠工,后期剪辑中,他的镜头可能会被大量剪掉。
平台的强势地位增加,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公平。2017年,制作成本3亿的网剧《如懿传》卖出8.1亿的独家网播价。“制作公司只要把剧卖出去,它就一定会赚钱,演员只要出演了,也一定会赚钱。”但是平台承担了所有的风险,“可能因为演员吸毒、嫖娼、出轨,导致这部戏没法播出了,或者这部戏播得特别不理想,亏了2个亿,这些跟演员和制作公司都没任何关系。”
如今形势变了。许多平台在购买影视剧前,会学习票房模式,与演员、制作公司签订一个风险共担的三方协议。“在拍戏之前,就会跟演员签协议,要求其在基础的道德层面不能出现问题。一旦出现问题,要赔偿损失。”2018年高云翔和范冰冰共同出演了成本高达5亿的《巴清传》(前名《赢天下》),随后,高云翔被曝在澳洲涉嫌性侵,面临巨额赔偿。为减少损失,2019年5月,高云翔与妻子离了婚。
“以前艺人是稀缺资源,平台要捧着他;现在平台是稀缺资源,演员要求着平台。情况完全变了。”王凯华说,平台有了分割资金的权力,会把钱用到更多、更需要的地方,“同时,也有了要求、制约、规范演员行为的权力。”
从业人员普遍“过劳”
高以翔之死,在影视行业内外都引发了程度不一的震动。结合2019年讨论热烈的“996”“熬夜死”等社会话题,许多人将之聚焦到“影视行业过劳”的问题上,而高以翔成为全社会加班、过劳的一个代表。
苏蒙克说,她的朋友圈里,浙江卫视的编剧导演同行经常在凌晨四五点发类似“上半夜录节目,下半夜开会。过俩小时还得开始录”的状态,配图则是凌乱的会议室和无比疲倦的导演们。
影视行业里,导演熬大夜,连开十个小时的会,后期剪辑工作到半夜,直接在机房睡,这些都是常态。而苏蒙克自己,也曾在一个月里,每天凌晨两三点回家,早上七八点又到台里。“能怎么办?所有人都这样,只能生扛着。”
相对而言,电视电影遭受的创痛则更为严重。“电视台要比我们这种做综艺的稳定很多,幸福很多,员工也是有固定薪水的。”影视摄影师张艾说,演员在综艺节目里能挣到更多,按照设计好的台本走,吃的苦也比演戏少。
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、沟通效率低等,导致拍摄时间被无限拉长,加班成为自然。演员之外的技术和工作人员,甚至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。“演员还好点,一般有上下班时间,但摄影、灯光、化妆,都是提前2个小时到,完了还要收场。”青年导演杨启后在横店拍戏的一段时间,一些工作人员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,有时候干脆不回宾馆,直接睡在片场。
杨启后和张艾都对国内流行的开机仪式心怀不满。“开机仪式要看吉利的日子,有时很耽误时间。”不仅如此,剧组里还流行“女人不能坐箱子”的说法,“据说女人坐了镜头箱、苹果箱,会沾湿气,因为女人的月经是污秽的,会给剧组带来不好的运气。”杨启后说,有身份的女演员不小心坐了箱子,会被提醒,一般女性坐了箱子,则会被严厉责骂。如果拍摄出了问题,比如杆子倒了、票房不好之类,就会归咎于坐箱子的女性。“这些,全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。”
明星耍大牌的现象依然存在。张艾曾参加一部宫廷戏的拍摄,片酬1亿元的女主演经常耍大牌,“什么睡美容觉啦之类的荒谬要求,还有提前不背台词、现场背。这导致拍摄进度严重延误,“后期只能疯狂追赶进度,天天熬夜,导演都熬不住了,然后换副导演监工,我们底层的弟兄有好几个都累晕了。”
他也和英国的剧组合作过。全剧组员工和演员同吃同住,所有人都实行8小时工作制。“但我们剧组的拍摄量,一天下来是他们的5-10倍。”
编剧黄石说,2014年冬天,他们在东北拍摄,因为连续熬了三个大夜,剧组里人都是蒙的。“当时在高速公路上抢拍一段重场戏,一个场工不小心站到警戒线外,一辆大卡车飞速驶过,直接把他撞死了。”最后剧组和保险公司才赔了不到30万。“这个场工有两个孩子。”
杨启后看到的圈子里,每年都会有剧组发生猝死事故,“但因为不是聚光灯下的演员,而是普通人,所以大家都不知道,也不会上热搜的。”一些工作人员从脚手架上跌伤或摔死,许多编剧深夜写剧本,因为大量抽烟和饮用功能性饮料,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。这些,都是明星、热搜效应背后,大众看不到的“过劳”和事故。
2014年,杨启后导演拍摄了一部纪录片,他每月的工资只有4000块,“因为导演和演员有露脸的机会,觉得自己早晚有一天会熬出头,所以能接受报酬低一些。”而更辛苦的摄影、灯光等工作人员,收入可以达到12万至15万一年,“这就是为什么这么辛苦,他们还肯干。”
苏蒙克说,影视人熬到半夜,大脑通常是高度亢奋的。90后媒体人邵光宇的女友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做剪辑,近两年,女友经常工作到凌晨3点,打车回家后睡不着,在床上打“王者荣耀”游戏,直到天亮才睡。“我真的受不了,就分手了。”
“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熬夜却没有死?”苏蒙克说,这是因为影视人有调休期。“可能一个节目忙了两三个月,完了之后可以轻松点,休息一个月。”苏蒙克说,“但也不是完全放松,因为还要筹备下一期节目。”
苏蒙克觉得,中国综艺从抄袭台湾、欧美和日韩,到后来有了版权意识,“买模板”,进步是很明显的,但代价是无法顾及影视行业人员的身体。“这不就是我们要的中国速度、拼搏精神吗?所有人都自愿加班,所以我们的节目水平、制作效果才快速增长。咱们的发展,就是靠不断压榨人取得的。劳动法、加班费,谁见过?”
可惜的是,中国节目始终缺乏创意,而创意和努力往往是矛盾的。“就是因为我们太努力了,才没有创意。”苏蒙克说,“搞创意的人全都在工作,他们根本没有生活,哪里来的好创意呢?”
影视业乱象
行内人都承认,明星“过劳”,实际上远不如幕后人员的“过劳”。而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,正是目前影视业存在的种种乱象。
杨启后说,影视行业中,普遍存在着小作坊式的生产形式,制片人拉到资金后成立剧组,会将不同工种转包出去。在预算太少的情况下,层层转包,往往导致拍摄质量、安全系数的下降。
杨启后举例,一部1000万投入的小成本电影,制作人截留300万甚至500万,再分摊给各个部门,而后续每个部门会继续克扣。“层层转包下来,落到拍摄上可能只有200万。要用200万经费做出1000万的效果,你只能把下面每一个环节都压榨到极致。本来一天拍8个小时,现在一天要拍20个小时,才能勉强到人家要求那个样子。”
“比如某个老板打算投资一部电影,他找影视公司,影视公司找制片人,制片人去‘拉皮条’,找编剧、导演、演员,然后讨论如何分摊资金。然后各个部门的老大,比如摄影指导、灯光师、化妆师,再去拉自己的部下。拿到多少钱,也是老大事先谈好的。”张艾说,这些老大、群头其实就是包工头。
杨启后曾经给一个道具组50万经费,包工头实际只花了10万。“做出来的内在质量,其实是有安全隐患风险的,但外界还看得过去,只要没出事情,就是很好的。”
但在其他方面,影视行业又存在许多腐败现象。张艾说,国内影视剧组中,层级关系非常突出。其中权力较大的是制片方、导演和大牌演员。“制片方相当于给编剧、导演、演员及经纪公司‘拉皮条’的‘皮条客’,油水最大。”制片方又分生活制片、现场制片、外联制片等,“他们负责给钱,上下打点,疏通关系。比如你去某个商场拍摄,商场不同意,外联制片撒钱解决。所有剧组中的不公、过劳,主要基于这种畸形的层级关系。”
有时候,剧组还要和官方打交道。“比如要租借某个政府机构的房子,监狱、行政机关大门口之类,这个时候官方要摆架子。”张艾说,“怎么摆平呢?要么塞钱,要么给他的子女上镜机会。”
许多从业人员都是关系户。“比如一个灯光组,包给了一个小老板,他找来一帮乡亲、兄弟来做,这些人根本没有经过专业的影视培训。你跟他说一个灯光效果,需要描述很久,现场还要不断调试。”杨启后说,“美国好莱坞有他们的影视流程,工会体系、教育体系也很发达。他们操纵摇臂的人,可能是南加大理工的一个硕士,而我们摇臂的人,可能高中都没有读完。”
一般的影视剧组中,个人签合同的只是剧组中几位核心人员,其他工种的人员,只由部门老大或群头代签集体合同。这样的合同,形同虚设。
因为转包和克扣,影视剧组里的器材质量经常不过关,有时临时搭建的三合板摄影棚刷完油漆,甲醛严重超标。“甚至会令人昏过去,我身边接触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。”张艾说,“有一次当地消防局过来把我们摄影棚查封了,最后靠外联塞钱了事。最后影片结尾还会出现:某某市某某公安局、某某消防局协力制作。”
克扣截留资金,导致剧组人员的伙食也很差。张艾说,剧组人员习惯吃馒头,因为馒头保质期长,可随身携带、扛饿,不容易坏。“饭可能经常是馊的,菜里可能有指甲头发创可贴,而肉是不能吃的,有时候还会有虫子。加上工作时间混乱,许多人因此得了肠胃病。有一次张艾剧组里的日本导演来拍戏,直接网购方便面,吃了三个月。
“生活制片克扣食宿经费,已经是国内多年来屡见不鲜的恶习,即使是导演和演员,对此也非常无奈。”张艾说,“账面上15块钱标准的盒饭,实际上成本不过三四块,你想想这还是人能吃的吗?”
张艾始终认为,演员还是要从作品出发,而不是什么综艺节目。因为失望,他放弃了过去从事多年的现场摄影,开始自己写剧本。
要解决这些腐蚀影视行业的问题,张艾觉得需要引入净化力量,比如工会。在他接触的外国剧组中,各个工种薪酬差别不会很大,也不存在克扣问题,账目都会报有关部门公示。
“任何行业没有这个,都是不会有希望的。”张艾说。
(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