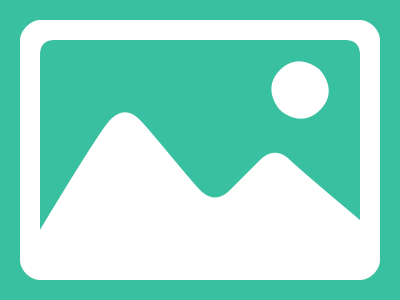01
老何是个律师,刚刚在街上挂出自己的牌子,正是要大干一番的时候,妻子却在这当口病倒了。没办法,老何只能一边忙案子,一边抽空到医院照顾。
来了几天医院,隔壁病房的一对乡下小夫妻引起了老何的关注。
听护士说,他们是刚成婚的小两口,头天晚上进的洞房,第二天新娘就病倒了。
一查,新娘患的竟是一种不治之症,医生说最多只能活六个月。也就是说,这对小夫妻注定只能做一晚上的夫妻了。
这天,老何照顾完妻子出来,刚好看见隔壁
完,过了十一才来报到。而且他不跟我们住宿舍,自己在外面租房子。他并不是天津人,听说家里在三河市开了个钢铁厂,是个富二代。
那时候还不流行讲“富二代”,我有个同学广东东莞人,老爸是全国人大代表,自己是家族企业的董事,隔一阵子就坐飞机回去开董事会,可依然跟我们一起住八人间,吃喝拉撒睡,走路放屁玩,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派头。张枭男却有点冷漠不近人情,独来独往,早上的课很少按时到场,晚上也很少跟大家一起上自习。
我一直记得他第一次走进课堂,留给我的印象。当时是班级辅导员把他介绍给大家的,他的名字让我们交头接耳了一会,然而让我惊诧不已的是,我发现他长得有点像李俊基。十一假期里,我在网吧里通宵上网,看《王的男人》,大户人家的老爷把孔吉叫到房间,抚摸他洁白光滑的后背时,我把手偷偷伸到裤子里,按捺不住地撸了一发。这是可以被原谅的,我还没谈过恋爱,连女人的手都没有摸过,十九岁,正是年轻小伙火力壮的年纪。所以看到他的那一眼,我内心感到了深深的自责。
还好他除了上课基本上不会出现在我眼前,否则我肯定会英年阳痿。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交谈还是班里组织的一次K歌活动,就在学校的红房子外。
我记得在那个大房间里,我们班上将近三十个同学挤在一起,当麦克风传到我手上,我本不想唱,可是宿舍的哥们喊道:“小桂子,来一个‘姑娘姑娘,漂亮漂亮’。”因为我经常在宿舍放一些摇滚音乐,他们耳濡目染,就来调侃我。不明所以的男同学哈哈大笑跟着起哄,女生们转过头窃窃私语。我当然不加理会,看到有许巍的《蓝莲花》,唱完就走出红房子,点根烟抽起来。
不一会儿他也出来了,站在我身边。我一看是他,有点不好意思。问他:“抽烟吗?”
他说:“来一根。”我抽出一根中南海,凑近给他点火,看到他白皙的手指,又想起李俊基光滑白洁的后背,颤颤巍巍地把火点上。没想到他刚抽了一口,竟然被呛得咳起来,眼泪都出来了。
他把烟递给我,说:“好难抽,还给你。”我怔了一下,把手里快抽完的烟扔在地上,接过他的烟,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,转了两下,放在唇间吸了一口,深深吸进肺里,吐了出来。
他问我:“你听过《我开始摇滚了》吗?”
“当然,”我说,“我不喜欢。”
“那个乐队就是天津的。”
“天津还有摇滚乐队?我还以为这里是文化沙漠呢。”那时候我年轻,没见过世面,却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
“我们可以一起去酒吧听现场啊。”他说。
“酒吧?”我从来没去过,以为是那种有长长吧台的酒吧。
“贵吗?”我说。我是个穷小子,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五百块钱。
“我请你。”他爽快地说,声音在夜色中无比温柔。
一天,张枭男告诉我说正午阳光乐队要在某个酒吧驻唱,让我和他一起去。我问他:“正午阳光是哪个乐队?”他白了我一眼,说:“就是唱《我开始摇滚了》。”我忙“噢噢”地点头。
下午我们在学校吃完饭,就坐公交去市里。酒吧里早就排了很多人,我们站在楼梯道上等着。我是第一次来这种场所,感到新奇,特别是有许多貌美姑娘,看得眼花缭乱。张枭男突然说:“交个女朋友,还是养条狗。”我说:“交个女朋友。”他又鼻子喷气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等了半天才放人进去,开始是两个本地不知名的乐队暖场。终于轮到正午阳光登场,人群中热闹地叫喊着:“我开始摇滚了。”这让我觉得颇没有面子,想找条地缝钻进去。还好王宝没有唱这首歌,先是一首《秋孩子》,一下子将气氛平复下来。我发现自己还挺喜欢这首歌的,主唱的声音也是我喜欢的,有一种优雅的沙哑、婉转。后来唱到《正午阳光》和《红蔷薇》,我才真正被打动,改变了之前对他们的看法。
我听到张枭男轻轻地跟着哼唱:“我是好美好美的红蔷薇,可恨老天不作美,被摘去花蕾,被剥去花蕊,可悲送人作玫瑰……”他的声音不是那种沙哑的,有点像张信哲的女声,我再仔细一看,发现他的喉结也不是那么明显。下意识里,我摸了摸自己突出的喉结。我又想起了《王的男人》里面的李俊基,王后说他“比女人还媚”,我看张枭男也有点像女人。想到这里,我赶紧摇摇头,把脑子的想法甩出去,“结束这场最温馨的折磨”(《我还是走吧》)。
音乐一直到十点左右才结束,人群散开。我们走在初冬的大街上,呼吸到清新凛冽的空气,头脑也变得清醒起来。我问张枭男住在哪,他说在王顶堤。我看时间有点晚,回到宿舍大门肯定关了,就问他能不能去和他挤一晚。他马上变得有些紧张,支支吾吾地说:“我那太乱了,地太小。”他又说:“我给你钱,你打车回去。”
很显然,他不愿意让我留宿,我就不再勉强,说道:“给我一百块钱,还有门票钱,我一块还你。”
他边翻钱包递给我一百元,边说:“我请你的,不用还。”后来我拿着多余的钱在网吧开了一个通宵,看看电影,睡了一觉。
接下来有些日子,我们没有一起聊过音乐。我感觉到他似乎有意在躲避着我,上课也不和我坐在一起,做实验时跑到别人的小组,显得格格不入。当时有个女生总爱带着另一个女生跟我一组,次数多了,其他同学就自然把实验台让给我们。那个女生的QQ昵称叫什么公主,同学有事没事就喊我“驸马”,搞得我想打人。
在感情上,我根本没有开窍,你总不能说欲望就是爱情吧。公主长得不好看,脸上还有麻子,肉乎乎的,我一点欲望都没有。但我又不是那种能狠心拒绝别人的男生,就这样一直拖到期末。
考完最后一门课,张枭男背着挎包在教室外面等我,说晚上请我吃饭。我们来到校西门外的小饭馆,点了三个菜:木须肉、地三鲜和水煮鱼。他说:“喝点酒吧,庆祝考试结束。”
我问他:“抽烟吗?”他连连摆手说不要,我就一个人抽着。我心里暗暗高兴,起码他没有忘记我这个朋友,我们还能坐在一起聊天,交流共同的话题。他虽然不会抽烟,但酒量却好得很,我喝了两瓶啤酒就晕晕乎乎,他干完三瓶还口齿伶俐,面色红润,笑靥如花。
他和我谈起一个音乐节,听起来像“谜底”,他说是“迷幻”的“迷”,“吹笛子”的“笛”。我虽然自诩爱好摇滚,但也只是听过魔岩三杰、许巍、汪峰鲍家街之流,像痛仰木马夜叉新裤子这些鬼名字的乐队根本没听说过。张枭男来了兴致,说个没完,滔滔不绝,最后他说:“明年迷笛音乐节我们结伴去吧。”没等我答应,他又说:“我请你,请你睡觉,哦,不是,请你住宾馆。”
聊到九点多,他说:“走吧,等会宿舍又要关门了。”他付了钱,和我一起走到校西门。我扶着他的肩膀,想搂住他的脖子,好让自己走稳。他一把抓住,把我的手从他胸前拿开,放到后面,左手拉着我的右手。他的手指修长,冰凉。我的左手搂着他的腰,他的腰肢柔软,他的右手搂着我的腰,这个姿势有点怪异。
摇摇晃晃到了校门口,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,说是送给我的。我拿来一看,是李皖写的《我听到了幸福》。我说了声“谢谢”,他说“不谢”,就告辞,打车走了。
整个寒假我都在看张枭男送给我的书,认识了很多摇滚和民谣歌手,还有一些歌手的轶事。
尹吾的《出门》是卡夫卡的一篇小说,胡吗个的专辑名叫《人人都有个小板凳,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》,以及高晓松、崔健、王菲的各种音乐历程,真是让我这只井底之蛙大开眼界了。在看这本书的时候,我总想起那一夜,我和张枭男勾肩搭背地走在学校西门外的小巷子里,两边是栉比鳞次的小饭馆和家庭旅馆。他的手指啊,真是冰凉;他的腰肢,为什么那么柔软?我不敢再想了,赶紧看着墙上挂的美女挂历。
一个月不知不觉过去,我们又回到了学校。张枭男和我的关系也正常了,我们上课坐在一起;晚上他偶尔过来上自习,我们挨着听一个MP3,一人戴一个耳机,把《我听到了幸福》里的歌手的歌都找来听,好像我们真的听到了幸福;做实验也凑到一组,公主见我对她没有兴趣,也不来黏着我;同学们依然拿“公主”、“驸马”开玩笑,只是驸马换成了另一个班的男同学。
“五一”越来越近,我和张枭男准备着去北京看迷笛音乐节。担心头两天人多,所以我们决定去看五月三号和四号的场。
三号那天,我们坐城际列车到北京,辗转来到海淀公园。里面已经散落了许多人,围着几个台子,比划着“rock&roll”的手势(后来我听别人说这个手势是女性在自慰,可我根本想象不出来)。错过了前面两支乐队,第三个是麦田守望者,他们刚出了一张新专辑,可我嫌他们的音乐有点流行,过于欢快,上一张专辑《save as》比较纯粹但又过于校园。
我问张枭男看过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这本书没,他说看过,我们相视一笑。接着是重塑雕像的权利,完全是英文歌词,但现场却能带人进入一种迷幻的境界。乐迷们摇摇晃晃,兜兜圈圈,我也拉着张枭男的手跟着跑起来。到了晚上,脑浊和AK-47乐队才将气氛推向高潮,大家都蹦蹦跳跳,吼叫,有情侣在聚光灯下拥吻,在地上打滚。我趁机搭讪了几个姑娘,介绍给张枭男,一直到九点多,兴尽而归。
出了公园,身体内的细胞还在跳动着,我们决定去北大转转,看看未名湖。校园里虽然有路灯,但依然黑黢黢的,走在未名湖畔,我突然想跳下去洗个澡。我问张枭男:“老舍是在这里跳湖的吗?”他说那是太平湖。
“那王国维呢?”
“颐和园。”
我想到了一个北大诗人戈麦,好像也不是在这里跳湖的。五月,天气已经转热了,我脱了牛仔裤和T恤,试探着下水。张枭男在岸边叫着:“小心点,别淹死了。”我下去游了几下,发现湖水并不深,看来没有人是在这里淹死的。
这时,远处有一盏手电朝我扫过来,保安跟着大喊起来:“谁在那游泳,赶紧上来!”边喊边朝我们跑过来,我麻利地爬上岸,顾不上穿衣服,就跑起来,一口气溜出校园。
我还穿着内裤,紧紧地贴在下身上。张枭男看了看我光溜溜湿津津的身体,说:“赶紧把衣服穿上,别让人当做流氓。”
我说道:“两个男的谁当我是流氓啊!”他懒得理我,转过身自个就往前走了。我穿好衣服,赶紧追上去。
回到宾馆,我想立马洗个澡,因为内裤贴着很不舒服。张枭男说他先上个厕所,说着就钻进卫生间,关上门。我脱下全身衣服,把电视打开,等他上完厕所。他一拉开厕所门,看到我一丝不挂的样子,睁大了眼睛,差点捂着嘴巴尖叫起来。不过马上又恢复正常,转过头,嫌弃地说:“也不注意一下形象。”
我也不当回事,说:“澡堂里没见过男人啊?”赤裸裸地走进卫生间。好像想起什么,问他:“你刚才大便还是小便啊,这么快,也用不着关门吧。”站在莲蓬头下冲洗着头发,我模模糊糊地听见他说:“你说什么,刚才说什么?”
我洗完澡又赤溜溜地出来,叫他洗了。他说不洗,累了想睡觉。我懒得管他,自己钻进被子里。我们订的是一个标准间,他和衣躺在右边的床上,见我盖着身子,就说:“你知道宾馆的床单有多脏吗,小心感染皮肤病。”听他这么一说,我倒真有点害怕,赶紧把T恤穿上。可内裤还湿着,就把它挂在空调口上,到早上肯定能吹干,牛仔裤就挂着空挡吧。
黑暗中,不一会我就睡着了。可能是白天玩得太疯狂,我的梦里也是数不清的人,男男女女,手拉着手,拥抱接吻。最后偌大的场地只剩下我和张枭男,我又看到了那天晚上的场景,我搂着张枭男的腰,他抓着我的手,彳亍(编者注:chì chù,意思为慢步行走)地行走,相互扶持着。半夜我醒过来一次,在幽暗中,透过电视和空调的微光,我看到张枭男睡得那么香甜、静谧,他的睫毛那么长,鼻子精巧,嘴角还微微翘起,眼珠子动了动,梦里不知看到了什么。
第二天依然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,不仅看到新裤子和夜叉,还有李志、张玮玮和周云蓬。因为是最后一天,乐迷们更加疯狂了,他们在听爱听的歌,做爱做的事,我也拉过不知多少女孩的手,肥的瘦的,美的丑的,和多少兄弟们拥抱,一起呼喊、跳跃,一直折腾到十点多,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这两天,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吧。回到宾馆,澡也懒得洗了,和衣就睡了。第二天,我们坐火车回到了天津。
那年五一还是七天长假,收假了张枭男也没有来上学,到了下旬才回来上课。也不怎么听讲、上自习,总是拿着一本雅思试题在看。他似乎要留长头发,我感觉有四五个月没理发了,看上去就像一个艺术家,映衬在他那俊秀的脸上,更像一个女人。其实我本来也是想留的,留了半年,过年回家被我舅舅揪着去理发店给绞了。我问他是想出国吗,他说只是准备考试,可能毕业以后去吧。
学期末大家都在复习、准备考试,张枭男又消失不见了,期末考试也没有参加。直到最后一天中午,结束所有的科目。他在我的宿舍里把我叫出来,让我去他住的地方帮忙收拾下行李。话语间,我感到他的情绪和表情有些怪异,想知道将要发生什么,就随他一起去了。
路上,他告诉我,下半年要去美国念书了。原来他并没有考上这所大学,家里利用了关系,把他送进来,只是为了提前适应大学生活,同时还能专心复习雅思,准备出国。而他还有另外一个秘密,想在离开之前告诉我。
他住在王顶堤一个居民小区里,租下了整整一套房间。空着一间小卧,大厅里也没有家具,他带我进了他的房间。一进卧室,里面的摆设物件和装饰彻底把我弄迷惑了,好像进错了房间。窗帘拉开了一半,微风穿过纱窗轻拂着,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,稍微才适应过来。墙上贴着粉红色的壁纸,床单是米老鼠的饰纹,床头居然摆着一个白色的熊娃娃。他的行李箱躺在地上,里面衣服满满当当,我看到了花花绿绿的内裤。
我的脑子有点乱了,想起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,霍尔顿在旅馆看到对面房间的男人试穿女人装束,还照镜子。他说:“这家旅馆确实住了满心理变态的人,我也许是这地方唯一的正常人。”后来我又看到卡佛也写过一篇类似的小说,讲一个男人给邻居看家,把邻居女主人的衣服拿出来试穿,并且在屋里走来走去。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的男人喜欢扮女人,而女人喜欢女扮男装。
张枭男站在窗前,背对着我,缓缓脱下红格子衬衫,他的肌肤是那样的光洁白皙,腰部线条玲珑,腋下却是一条白色的束胸。我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,全身控制不住地颤抖。她(我已经猜出来了)脱下束胸,前面隐隐有影子跳脱束缚。慢慢地,她转过身来,她的胸前是一对小巧的乳房,我想起《圣经•雅歌》里的话“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,就是母鹿双生的。”此时,我已经不能自持,瘫坐在床。她接着脱下了牛仔裤,里面是一条淡蓝色内裤……
她像一朵含苞的花儿,在光与影中开放,头发已经遮住了耳朵,锁骨玲珑,没有喉结,窄小的肩膀在微微颤动,内腔的跳动带动着胸前在起伏,她的肚脐眼很好看,如一口幽泉,让我恍若隔世……在这正午的阳光里,“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岗去,直到天起凉风,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。”
抢先看更多精彩情节?iPhone可到app store,安卓可到各大应用市场,搜【每天读点故事】app收看。也可加微信dudiangushi收看。